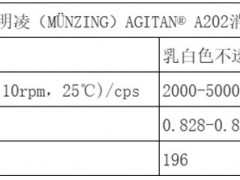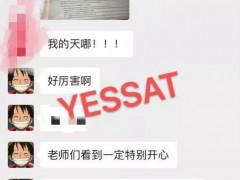高等教育现代化要破解三大难题
【思想汇】
编者按
今年2月发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了到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推动我国成为学习大国、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的宏伟目标。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作者认为,过去几十年我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为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积累了不少经验,但要实现2035年的宏伟目标,还需认真思考并解决知识生产的体制化、大学治理的行政化、学术评价的量化导向这些促进着高等教育发展但同时逸出负面效应从而困扰着高等教育的三大难题。而破解这些难题,是高等教育回应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的“要深化办学体制和教育管理改革,充分激发教育事业发展生机活力”必须作出的切实有效的探索,这一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不仅将有力助推中国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也将为全球高等教育解决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和普遍性难题提供借鉴。
1.知识生产的体制化与反体制化
人类知识和文明不断发展和扩大的历程,也是一个知识生产行为和过程被不断体制化的历程。这种体制化,在价值观念方面,体现为确立了知识生产的独特价值,宣告了知识生产作为人类社会重要生产方式的合法性和优先性;在组织架构上,体现为建立了进行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各种专门机构,比如大学和各类科研院所;在制度安排上,体现为形成了一套与知识生产、传播与应用相适应的明示或潜在的社会规则,包括知识分类与学科划分、范式和学术共同体、知识生产过程、人才培养与成果评价、投入机制,等等。
知识生产的体制化使得大规模的知识生产成为可能,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交流、传播与创新,也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整体福利。可以说,没有知识生产的体制化,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如此快速地进入现代化。但是知识生产的体制化在积极促进知识生产的同时,消极的一面也日益显现。比如知识的学科化,在推动知识专门化深入化的同时,人为制造了不同学科之间的藩篱,导致了知识的分离;而学科范式、学术共同体和科研体制的形成,无疑宣告着某些知识生产方式和某些生产人员的优先性,使得社会资源能够流入这些领域这些人员的生产活动,而没有被纳入范式和体制之内的知识、问题和人员则被排除在外,导致了知识生产的固化和知识创新的变缓。
但是,知识本身是灵动的超越的,从来不会给更有权势更有财富者更多发现新知的机会,有时反而是那些超出现有体制和思维束缚的人,有着更大的发现潜能。所以知识生产在被体制化的同时,总是有着反体制化的倾向。这种反体制化的倾向,一直交杂在知识生产体制化的过程中,并随着人类认识世界能力的加强,越来越明朗。20多年前,英国学者吉本斯等人在社会观察中发现,在传统的、人们所熟知的知识生产模式之外,正在浮现出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这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不仅影响生产什么知识,还影响如何生产知识、如何组织和激励知识生产、如何监控和评价质量。相对于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新模式的研究问题在应用情境中提出,而不是由某个特定的学术共同体主导;新模式无论从人员、过程还是研究方法来说,都是跨学科的、异质的,与传统模式基于学科的、同质的取向不同;相对于传统模式在组织上的稳定结构和等级制,新模式的组织设计更加多变和非等级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是对传统知识生产体制化的一种反动,体现了知识生产冲破体制束缚的努力。这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近年来在一些高科技企业已经被广泛应用。
但是,作为知识生产、传播与创新重镇的大学呢?尽管这些年来,一些大学力图通过建立跨学科组织、各类综合性智库和协同创新中心来突破原有体制的约束,并主动去拥抱慕课、微课等新的知识传播方法,但学科化、同质化的传统知识生产模式依然在大学中占据统治地位。正如人们总是很难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大学如何作为高度体制化的产物,去突破体制化的障碍,回应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带来的挑战,是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2.大学治理的行政化与过度行政化
近些年来,中国大学治理的行政化问题饱受人们诟病。事实上,大学治理的行政化并不是中国社会独有的现象,而是当前世界各国大学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只是由于中国社会处于转型之中,使得这个问题更加突出。这个问题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高等教育大众化、新公共管理主义的盛行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知识经济和高等教育大众化把大学从以往社会的边缘转置于社会的中心,政府和社会对大学的关切度前所未有,投入力度也前所未有。高关注度和高投入力度自然就带来对成果和绩效的高期望值,加上新公共管理主义的推波助澜,大学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社会问责。大学内的单个学者或是系科并没有能力代表大学回应社会问责,因而有可能代表大学整体来对社会问责进行回应的大学行政层兴起,大学校长不再只是学者的代表,同时还担当政府或社会的代理人。为了促进学者和基层组织的生产以回应问责,大学的行政系统和行政管理职能不断加强。所以,过度行政化从某种意义上是大学现代化的一种必然。
但是,大学的主要功能还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利用知识服务社会、传播文化,学者们从事的是需要创造力的学术生产,而不是标准化的物质生产,科层制的行政效率常常并不能带来学术效益。管理学大师明兹伯格等经过比较认为,大学这类专业组织与传统科层组织不同,并不适合一般科层制的管理模式,因为:第一,与传统科层制聚焦于权力顶端不同,由于受到教学科研工作性质的影响,大学运行有权力下沉的特点;第二,知识生产的分工使得学者的工作普遍有双重忠于现象,他们在忠实于自己的工作单位的同时还忠实于自己的专业和学术共同体;第三,学者们在日常工作中彼此相对独立,但与自己的服务对象比如学生、某个基金或合作单位关系紧密;第四,学者们的成果是在共有的知识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探索和经验,实现了个性化的转化,所以难以统一要求和进行测量。
显然,为满足知识生产需要形成的学术文化与回应社会问责需要形成的行政文化在价值取向上有着不同,因而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与冲突。学者自由散漫、自行其是的风格让行政管理者头疼不已,而行政管理者标准化、功利化的管理倾向也被学者们抱怨不休,认为约束了学者探索知识的热情。如何解决或调和行政化与过度行政化之间的矛盾,是体现大学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的重要问题。
3.学术评价的科学化与伪科学化
在去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从而将解决教育评价问题上升到了党和国家关切的高度。“唯论文、唯帽子”正是针对学术评价而言。
一般认为学术评价的问题,是评价方式不够科学带来的,但当前学术评价问题的根源,恰恰是对所谓科学化的追求。随着人类进入以经验和实证为主要方法认识世界的时代,科学常常被定义为一个建立在可反复验证基础上的知识系统。越是依赖于可计量的经验数据的知识,被认为是越“硬”的科学。当前的学术评价大多也采取了这种工具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倾向,人们寻找各种量化的工具和方法来对学术进行评价,比如,计算论文发表的数量,对学术期刊进行人为的等级划分,计算获取项目和基金的数量甚至金钱的数量,对学者设置各种奖励各种“帽子”,对学科学校设置各种权重各种赋值。
但是学术真的可以用这种形式主义的量化方式来进行评价吗?我们知道,学术研究的本质是探索知识,是一个不断探求未知的过程,用有限的已知来评价对无限未知的探索,显然就有认识论和逻辑上的悖论。探索未知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人们很难事先断定什么是正确的或有效的探索。正如爱因斯坦所言,“科学史表明,伟大的科学成就并不是通过组织和计划取得的;新思想发源于一个人的心中”。前些年一位日本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的创新就在于不小心把试剂错误地放入了某个既定的实验当中,而首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伦琴关于X射线的传奇发现更是为人们津津乐道,这种因为“失误”或“偶然”带来创新的故事常见于科学史,其实就从一个角度强调了创新是对陈规和已知的突破。所以,学术研究的本质决定了它应该是一个自由探索的过程,对其进行评价需要十分慎重,越是号称可以量化和标准化的评价就越是可疑,越有可能是披着科学外衣的伪科学。
要促进和激励学者的知识生产活动,似乎不能没有学术评价,但什么是真正科学的学术评价值得深思。比如,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人们认识水平的有限性决定了合格评价比优秀评价相对科学。认识世界是一个渐进过程,科学探索总是充满试错,人们往往先知道什么是错误的落后的,而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先进的,通过合格评价来避免一些已经被验证是错误的做法是可行的;但优秀评价评出来的未必是先进的探索,特别是优秀评价形成的导向很容易把人们引入科学探索的窄途,限制人们科学探索的视野和能力。
以上三大难题涉及大学这一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核心机构的三个根本问题,那就是:怎么组织知识生产?怎么运行管理?怎么评估效益?知识生产的体制化、大学治理的行政化和学术评价的“科学化”,本身就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产物,如何在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克服它们越来越扩大的负面效应,是不得不面对的难题。这些难题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而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中面临的共有问题。中国要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成为高等教育强国,就意味着在解决全球高等教育共同问题上有着切实有效的探索和先进的经验,有能力回答好这些普遍性难题并能够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
(作者:胡娟,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学院教授)